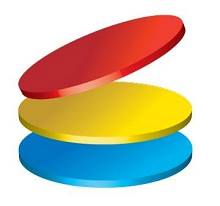- 14
- Oct
- 2016

▲示意圖/ShutterStock/版權所有,嚴禁轉載
(作者/卡翠娜.戴維斯: 住在英國西南部的康沃爾郡,喜歡衝浪和拉大提琴,亦曾在許多音樂節上演出,包括著名的格拉斯頓伯裡音樂節(Glastonbury)。現為創作歌手,發行過專輯《Ribbons》。)
我爬上岬角的頂端,周圍的氣氛非常超現實,馴鹿頂著牠們的大角從濃霧中隱隱約約地冒出來,後面跟著瞪大眼睛盯著我看的小馴鹿,小心翼翼地從成千成百的石塔中穿梭而過。
那些石塔數量之多,好像幾世紀以來只要有人曾經來到基夫斯克杰羅登,就會用石頭堆一個塔,證明他們來過。而我也不例外,我跪下來,從地上選了一些石頭,堆了一個屬於我的石塔,看起來非常適合這個環境。當我結束後站起來,發現濃霧已經開始漸漸退去,若隱若現中浮出地平線的輪廓。我站著觀看,直到濃霧完全散去,現在,我可以清楚看見太陽。
我希望可以找到適當的詞句,來形容濃霧散去後一切呈現的樣貌,但我想了半天,最適合的形容詞也許就是:普通。這裡的風景其實一點都不普通。大海抵著陸地,海面好像屏住呼吸般地平坦寧靜,地平線上方的天空呈現一片常見的帶狀金黃色,而那之上的天空,則是落日中常見的濃烈深紅,然而這片天空的其他部分卻呈現明亮的淡藍色,其中點綴著粉紅,就像黎明初起的感覺。
位在不遠處的北角,這個我嚮往已久的地方,看起來一點都不是我原先想像的樣子,反而像隻巨大的紅鱷,正要往北極的方向衝出去。天空並沒有繁星滿布,但太陽的確在水平面上不停跳躍著,像個默劇演員,一次又一次鞠躬謝幕卻遲遲不肯下臺。那一條帶狀金黃色在漸漸變窄、即將消失之前,又開始擴張開來,然後,太陽就在我眼前再度慢慢往上升,背後傳來鳥兒瘋狂的鳴叫,天色漸漸變亮,又是一天的開始,嶄新完美的一天就這麼從夕陽中蹦出來了。
我躺在潮溼的草地上,盯著頭頂那一動也不動、蓬鬆的粉紅色雲朵,就在一剎那間,我被一種從未有過的感受占據。那感覺就像是經歷一段漫長的爵士演奏,終於到了尾聲,鼓手最後一擊宣告結束,所有人才突然回過神來。
我把耳朵貼在地面上,聽著馴鹿咀嚼食物的聲音,然後坐起來,聆聽風平浪靜的海洋細細地呢喃,發現自己也喃喃自語唸著一段卡夫卡的名句。我只聽過一次就忘不了,因為它實在太美了,那段話是關於學習讓自己變得自在、安靜與安於獨處,因為當你可以自在、安靜地獨處一段時間,就可以開始看見這世界的原貌:「毫無保留,狂喜會像海浪般湧到你的腳邊。」
下一刻,我將臉埋入地面痛快地大哭起來。我終於辦到了,一切的崩壞和混亂都只是為了來看這個午夜太陽,而安德魯的死已是不變的事實,他永遠離開了,永遠都不會知道我成功靠著街頭表演一路來到北角,他也永遠不會知道關於強艾瑞克與亨利克的事,不會知道我曾經在多佛勒山耗盡汽油,拋錨在路邊。
我痛哭是因為我想回家,還有因為傑克跟一個甜美嬌小的衝浪女孩在我的棚屋裡做愛;我哭也是因為生命太美,但同時也像恐怖的雲霄飛車一樣永遠不停下來、不讓我下車,即使我知道最後我還是難免一死,而我所愛的人也都會死;我痛哭,是因為一旦人死了,無論你如何努力幫他們實現那些生前瘋狂的夢,他們也不會再回來。永遠。再也不回來。
我感覺自己仍然可以清楚的聽見安德魯的聲音,那麼清晰,彷彿他就站在我身後。
「哈囉?」
我放聲大哭。
「哈囉?」那聲音又問了一次。
我坐起來。
「哈囉?」那聲音問了第三次,只是這次聽起來完全不像是安德魯的聲音了,聽起來像是那個站在我後面大約兩呎遠的一個女孩子的聲音,她手裡拿著一個相機。
「很抱歉,我並不打算驚擾妳,我的名字叫做漢娜。」
漢娜看起來非常普通,除了她的頭髮,那簡直就像是在沒有照鏡子的狀況下,用拋棄式廉價剃刀自己剃的。她的身高跟我差不多,也許比我稍微瘦一點,一雙淺棕色的大眼睛讓她的臉看起來很漂亮,她跟我一樣穿著牛仔褲和T恤,背著一個小背包。不過漢娜可一點都不普通,她是那種搞不好一輩子只會遇見一次的特別之人。她的與眾不同,會讓你以為是我捏造出來的,但我發誓我沒有。
漢娜出身於羅弗敦群島,這是她其中一項特別之處。那是位於博德北邊、特羅姆瑟南邊的一列群島。我聽過人們談論羅弗敦群島,不只在挪威,甚至在我還沒出發前,我還在英國時就聽說過,那個地方有點像英國的夕利群島,是那種你無法想像有誰會從那裡來的偏遠小島。
「現在我住在倫敦。」
她舉起她的相機,那是一部沉重、看起來很昂貴的相機,她另一隻手裡拿著一個摺疊式三腳架。
「我是個攝影師,這也是我到基夫斯克杰羅登來的原因。我接了一個案子,要來拍攝永晝。」
其他讓漢娜顯得很特別的是,她總共有十二個兄弟姐妹,還有她大量地練習靜心打坐,已經達到一種開悟的境界(我是從傑克那裡學到開悟這個詞,他想要開悟想得不得了)。換句話說,她已經覺醒了,她是一個全然覺醒的存在,也許那說明了為什麼當你靠近她、圍繞在她身邊的時候,會有一種嗑了藥的感覺,讓你不再感覺恐懼,而事實上你也不再需要嗑藥了。
但關於她的事,我說得太快了。
因為方圓百里內只有我們兩個,所以回程的路上我們就一起穿越苔原走回去。這次我終於可以看清楚四周美麗的風景,有清澈湛藍的湖,湖邊的沼地羊鬍子草棉絮般的花在風中搖曳,看起來就像是白色的羽毛將生命寄托在脆弱的細桿上。
漢娜走路的速度很快。相機塞進她的背包裡,而腳架保持平衡的架在肩膀上,她只用纖細的手輕輕搭著,剛開始我們兩個都不太說話,大約走了兩小時後才在一個石塔處停下來,休息幾分鐘並喝點水。
漢娜問我為什麼哭,跟亨利克問的一樣,但當時我沒有老實的回答亨利克,我認為他不會理解,也或許是我根本不信任他。說到這,漢娜還有一點與眾不同的地方,那就是我非常信任她,即使我才認識她不到兩小時,就願意說出一切;當然,也許是因為我歷經了這些日子、經歷好幾個星期的沉默後,終於可以和人聊聊這件事,對我來說實在是一種舒解。
無論如何,當時我一開了口就再也停不下來。
我告訴她關於安德魯的事,以及他是怎麼荒唐地死去,之後每當我想起這些事又怎麼讓我感到暈眩,於是我莫名其妙的認定,如果我能為了他,一路靠街頭表演來到這裡看見永晝,也許會讓事情完全改變。
但實際上根本改變不了任何事情,如果硬要說有什麼變化,那就是事情變得更糟糕了;然後我告訴她關於傑克的事,告訴她,從前我是怎麼背著傑克的攀岩繩走到他常常攀爬的懸崖下,卻因為太害怕而沒有跟他一起爬;還有我常常跟著他到海邊,只是坐在沙灘上好幾個小時看著他衝浪,從來沒想過我應該自己也試試,直到我聽了關於那個甜美嬌小的衝浪女孩的事,不過這不是重點,重點是我對每一件事都怕得要死,包括海浪。
我告訴她關於這漫長的幾個星期在街頭表演的事,還有一開始我真的恨透了在別人面前演奏;我告訴她關於我喝得爛醉然後跟亨利克上床的事,而事實上他就是促成我來到這裡,與她一起步行穿越苔原的人。
當我終於敘述完所有的事情時,我們也回到了停車場,我靠在車上累得半死,這輩子從來沒有覺得這麼疲憊,我的兩條腿快癱了,我告訴她,現在我已經見識到永晝,一切都結束了。接下來,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怎麼過。
漢娜放下她的背包,只是微笑著說,「也許妳就要醒來了。」
(全文未完)
>>本文摘自《勇氣絲帶》一書
>>來信投稿vanchang@tvbs.com.tw、閱讀好文都在【T談談】粉絲專頁!
●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並授權刊登,不代表TVBS立場
●投稿、推薦作者、討論文章,歡迎寄至vanchang@tvbs.com.tw或上 T談談
人氣點閱榜

她真心奉勸女人這9種朋友別深交:背後講壞話、勢利眼、重男輕女...
 2017/06/20 12:53
2017/06/20 12:53
一定要有這9種感覺,這才叫做愛情!
 2017/09/25 12:43
2017/09/25 12:43
清大高材生面試遭打槍8次,第9次他才知道…
 2017/08/24 10:43
2017/08/24 10:43
想要讓男人愛妳,先從了解男人開始。
 2017/05/04 18:02
2017/05/04 18:02
吃地瓜減重卻變胖?營養師:這樣吃才能降低熱量
 2018/06/04 10:47
2018/06/04 10:47
生理期特別累?其實妳缺少這些營養!
 2018/01/17 14:23
2018/01/17 14:23
外食族必備「麵攤熱量表」,當心爆卡小吃!
 2017/12/26 10:49
2017/12/26 10:49
出差實用!5句海外協商談判英文讓你懂得Give And Take
 2018/03/06 14:50
2018/03/06 14:50
【偏執型人格】既自卑又自大,既熱愛又猜疑 !
 2016/06/02 10:22
2016/06/02 10:22